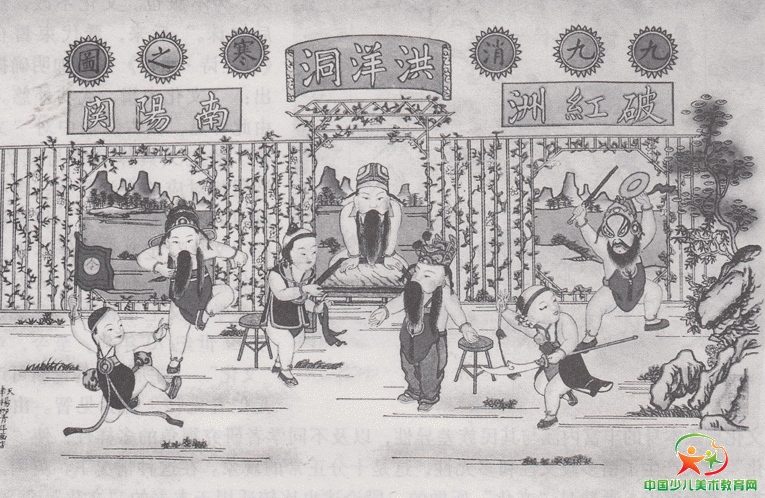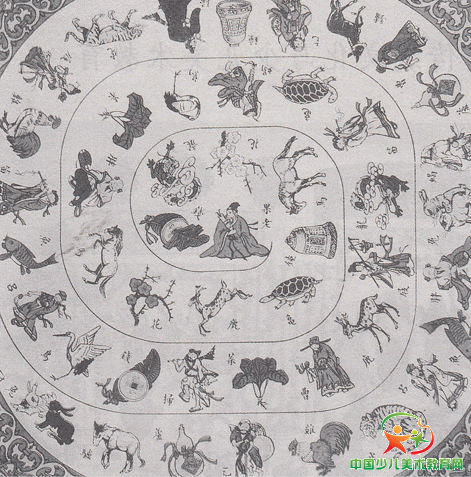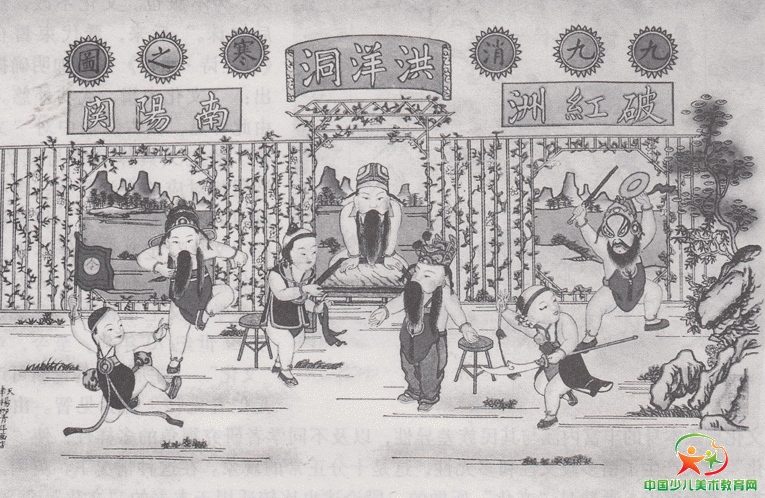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关于“文化”这一概念的定义,目前学界有160多种表述,说法莫衷一是。
在古代中国,“文化”这个词是由“文”和“化”两个单字组成的。这两个字远在殷代武丁至周代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出现了。最早见著于对“文”的论述是《易·贲卦》的《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里,“天文”指的是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人文”指的是社会伦常。意思是说,治理国家既要掌握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又要把握社会中的人伦纲常。进而转衍出“经纬天地谓之文”(《尚书·尧典》)、“文者,德之总名也”(《国语·周语》)、“物相杂,故日文”(《易·系
辞下》)、“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词谊(义)”(《释名·释言语》)等诸多语义所界定的“文”,呈现出人由原始的自在向自为进化、发展的历史轨迹。而“化”在古汉语中有变化、化生之义:“能生非类日化”(《素问·天元纪大论》)、“化,变也”(《后汉书·张衡传》)、“化,教行也。从匕从人,匕亦声”(《说文解字·匕部》)等。这些对“化”的词义界定,把“化”引申为以文德之治教化民众的社会含义,指教人则为化。正是在这样一些对“文”与“化”的具体表述中,使“文化”具备了初始的意蕴情境,体现出人的主动性与能动性对事物和现象多样性的整合与规范的理性精神。把“文”与“化”联结构成一个复合词使用的,最早见于西汉刘向在《说苑·指武》中的一段话: “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后来,晋代束皙在《补亡诗·由仪》中更加明确提出: “文化内辑,武功外悠。”由此可见,在古汉语中对“文化”的定义具体是指与武力、刑罚相对应的文治教化,含有鲜明的文明教化之义。将这样的“文化”定义运用于本书是十分恰切的。在西方,从近代人类学意义上审视文化现象始于19世纪70年代,至今,对“文化”一词所做出的论断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于文化现象本身的丰富内涵与其民族差异性,以及不同学者研究视角的多样性,使“文化”定义产生了诸多歧义性和多元性,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对“文化”所做的一段论述也比较适用于本书的“文化”含义。泰勒在其1871年出版的著作《原始文化》中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泰勒《原始文化》中文第1版第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